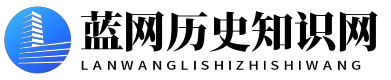了解一种文化的主导思想方式与了解这种文化的时间观有内在关联。这不仅仅是马丁・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的看法的一种延伸,而且可以在另外一些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家(比如尼采、柏格森、胡塞尔等等)那里找到这样那样的支持。按照这个思路,要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就需要知晓它所包含的时间观。这个问题到目前这止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时间的最主要两种看法,一是(目的论)的,二是物理自然的。前者来自教,认为真实的时间由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因此,时间或历史向着最终决定这种关系的那个终点--最后审判--而趋进。后一种时间观与人测量时间的精密手段相关。按照它,时间从根本上讲与人的存在与否无关,它是一种客观的、匀质的、不可逆的单向流逝,本身无意义可言,只是物质实体存在的一种方式。当然,二十世纪以来,在科学、哲学的新进展中,出现了新的时间观,尤其以广义现象学的时间观与我们有关。至于古代西方的或古希腊的时间观,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既不是的,又不(只)是物理自然的。其次,我们看到,古希腊的奥菲斯(Orpheus)教认为:时间(chronus)乃是运动与区别的本原,因而也就是万物和世界的本原;[1]另一种说法讲时间乃是收获之神。因此,后来的古希腊哲学中讲ldquo;生成rdquo;、ldquo;变化rdquo;和ldquo;运动rdquo;的学说可以被看作对于这时间本原的某种解释,而讲ldquo;数rdquo;、ldquo;存在是一rdquo;、ldquo;理念(相)rdquo;的学说则力图超出这种时间(即不再认时间为本原),或将时间凝固在没有ldquo;过去rdquo;与ldquo;未来rdquo;的ldquo;现在rdquo;之中。亚里士多德折衷二者,将时间定义为ldquo;关于前后的运动的数rdquo;。[2] 总之,对于古希腊人、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来讲,时间起码隐含地(implicitly)是个涉及本原的问题,但它在本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中极少作为一个本原问题得到直接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治ldquo;中国哲学史rdquo;的学者们往往是通过西方传统ldquo;哲学rdquo;的概念形而上学视域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所以,迄今极少有人能关注这种思想中本原意义上的时间问题。然而,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学偏见地阅读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就会强烈地感到ldquo;时rdquo;的突出地位。在那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生机勃勃的ldquo;时rdquo;代中,最智慧的人们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在别的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正如古希腊人对纯形式之ldquo;数rdquo;和ldquo;存在rdquo;之ldquo;相rdquo;的体验在其他文明中几乎不存在一样。
先秦人讲的ldquo;时rdquo;主要指ldquo;天时rdquo;,ldquo;敕天之命,惟时惟几rdquo;(《书・益稷》);[3] ldquo;天地盈虚,与时消息rdquo;(《易・丰・彖)。但这天时并不只意味着ldquo;四时rdquo;和ldquo;时制rdquo;(比如夏之时制、周之时制),而有着更微妙的ldquo;消息rdquo;。我们可以称ldquo;时制rdquo;、ldquo;四时rdquo;等意义上的天时为ldquo;天之时rdquo;,即天的时间表现,而称原本微妙的天时为ldquo;原发天时rdquo;或ldquo;原发时间rdquo;。所谓ldquo;原发rdquo;(originally happening),是指这时间不可还原为任何ldquo;什么rdquo;,比如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种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循环构合或发生。时间体验一定涉及ldquo;想象rdquo;,或者表现为ldquo;保持(已过去者)rdquo;,或者表现为ldquo;预期(将要到者)rdquo;;但原发的时间体验中的保持绝不只是对过去事情的ldquo;再现rdquo;,对未来事情的ldquo;预现rdquo;,而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相互依存着的当场呈现。当然,就是那时人讲的ldquo;天之时rdquo;也绝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和对这种时间的测量规定;它们源自阴阳、八卦、五行的理解方式,与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有内在关系。此外,有关天时如何体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学说也不只是邹衍和古文经学家们讲的ldquo;终始五德之说rdquo;,[4] 而有更活泼的和非定序化了的表达。
本文就将探究先秦人的ldquo;原发天时rdquo;观,展示这种天时观如何演变为各种ldquo;天之时rdquo;学说,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一.《易》的原发天时观
儒家的经书和另一些先秦子书,比如《孙子》、《老子》、《庄子》等,里边包含着对原发天时观的丰富精微的阐发。我们先来看一下作为ldquo;群经之首rdquo;且为儒道所共重的《周易》中的天时观,它对于中国天道思想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组成八卦的最基本单位ldquo;阴rdquo;(- -)和ldquo;阳rdquo;(---),并不只是ldquo;象征rdquo;两类基本的存在形态,更不能理解为两种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亚里士多德讲的ldquo;质料rdquo;;从字形上看,此两字都与ldquo;日rdquo;有关,字义也与日的向背和运行位置有关;故《易・系辞上》6章言:ldquo;阴阳之义配日月rdquo;。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日(与月)正是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关的ldquo;时rdquo;的来源。因此,《易》中的阴阳本身就意味着终极的相交和相互引发,由此而生出变化、变化之道和不测之神意。所以,ldquo;一阴一阳之谓道。hellip;hellip;生生之谓易,hellip;hellip;阴阳不测之谓神。rdquo;(《系》上5章)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就是这种阴阳本性的表现,在二爻、三爻和六爻的层次上各ldquo;通其变rdquo;、ldquo;极其数rdquo;,ldquo;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rdquo;
按照这种理解,易象的主要功能是在ldquo;通变rdquo;和ldquo;生生rdquo;之中显现出ldquo;天下之至变rdquo;。(《系》上10章)而这阴阳相互引发的ldquo;至变rdquo;对于中国古贤而言即原发之时。所以,《系辞》下传第一章讲的:ldquo;刚柔[即阴阳]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rdquo;ldquo;趣时rdquo;就意味着ldquo;趋向适宜的时机rdquo;。[5] 可见,ldquo;易rdquo;之变通绝不只是数理上的组合通变,而是指在此卦爻的变化势态(ldquo;趣rdquo;或ldquo;趋rdquo;)之中开启并领会到ldquo;时机rdquo;或ldquo;天时rdquo;。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即《易》所理解的ldquo;时rdquo;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也不是外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而是在错综变化的摩荡趋势中所构成或媾合而成的原发时间。ldquo;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rdquo;。(《系》下5章)原发时间或ldquo;易时rdquo;绝非线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更重要的是,这ldquo;相推而生rdquo;(《系》上2章)的原发时间必与人的ldquo;彰往察来,微显阐幽rdquo;(《系》下6章)之ldquo;知rdquo;不可分。也就是说,此原发时间乃是ldquo;时机rdquo;,得此时者必ldquo;知几(机)rdquo;,而能以ldquo;神rdquo;会事。ldquo;几rdquo;即变化之最微妙、最氤氲化醇、动于无形而得机得势之处。故ldquo;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rdquo;。(《系》上10章)ldquo;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rdquo;(《系》下5章)所以ldquo;知几rdquo;(《系》下5章)就是知时机,乃学《易》之第一要务。
当胡塞尔(E. Husserl)和海德格尔(M. Heidegger)以现象学的方式来研究ldquo;时间rdquo;时,发现这种原发意义上的(既非宇宙论的、亦非目的论的)时间除了各种ldquo;趋向rdquo;及其ldquo;相互媾生rdquo;之外别无他物,连ldquo;先验的主体性rdquo;也不能在这ldquo;赫拉克利特之流rdquo;中维持。然而,正是这毫无现成性可言的ldquo;至变rdquo;是我们ldquo;领会rdquo;或ldquo;理解rdquo;世界和自身的源头。《易经》和《易传》的作者们在这一点上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通,即深知终极实在是不可被对象化、实体化的,所以一再讲这样的话:ldquo;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rdquo;(《系》下8章)将组成卦象的六爻说成ldquo;六虚rdquo;,正说明卦象、卦理本身以机(几)变为本,根本不预设任何ldquo;元素rdquo;的存在,而是在ldquo;不居rdquo;或ldquo;不可为典要(典常纲要)rdquo;的ldquo;周流rdquo;和ldquo;出入rdquo;之中构生出象和爻之时机含义(ldquo;度rdquo;)。简言之,ldquo;易象rdquo;之义即时机(几)之义、时机之ldquo;度rdquo;。ldquo;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rdquo;(《系》下9章)。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易象无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部分都是ldquo;时物rdquo;,即原发时间的存在形态或构生形态,而不是任何现成的存在形态,比如已确定下来的象征结构和数理结构。其中总有正在当场实现之中的流动和化生,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程式化、哲理化和ldquo;电脑化rdquo;,而正在ldquo;化生着的rdquo;的境域就正是原发的时间或天时,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互中生成;ldquo;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rdquo;(《系》下6章)如果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易象即原本意义上的ldquo;现象rdquo;(Phaenomen),意味着ldquo;依其自身而显现自身rdquo;(das Sich-an-ihm-selbst-zeigen),[6] 就凭借自身中的各种变化趋势的而显示出自身的时机化含义。[7]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读《易》,就不仅能看出ldquo;卦时rdquo;、ldquo;爻时rdquo;,而且能体会出所有真切的解释方式中的时性。在《易》、特别是其中的《彖辞》里,ldquo;时rdquo;这个字大量出现,比如解释《乾》一个卦的文字中,ldquo;时rdquo;就出现了十多次,并且具有非常突出的诠释意义。尤其是在《豫》、《随》、《坎》、《革》等十二卦中,《彖》作者一再赞叹ldquo;时(或lsquo;时义rsquo;、lsquo;时用rsquo;)大矣哉rdquo;,表现出对ldquo;时rdquo;的重要性的深刻领会。《尚书》中也有大量的ldquo;时rdquo;字,但其中大部分被训解为ldquo;是rdquo;,只有少数可读为ldquo;时机rdquo;、ldquo;适时rdquo;。《易》中的ldquo;时rdquo;则大多应被理解为ldquo;时机rdquo;。